
陳渭清(Vivian Chen)
華附AP 2019屆畢業生,初中畢業于中大附中,在18/19海外大學申請中獲美國文理學院波莫納學院ED2、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羅切斯特大學(獎學金5000美元),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圣安德魯斯大學(本碩連讀)等院校錄取。
ED放榜的前一天,我在早早沐浴更衣完畢后,把五斤重的電腦抬到了床上,方便第二天查看結果。我九斤重的貓在熄燈后不久爬到了我的被子上。它在凌晨四點進食完畢回到我腳邊的時候被全身發冷的我飛踹,然后開始在家里各大房間進行連續十分鐘的巡回嘔吐表演。我拖地的時候想,按照人品守恒定律,如果四點的時候發生了麻煩事兒,那么七點鐘應該就有好消息了吧。結果早上一睜眼,看到的是portal里面被我詬病已久的棕色紅色搭配以及defer的消息。
高二的時候我總是以為申請季是一個浪漫主義者的旅程:小心翼翼地相中一所reach school作為夢校,每天在崩潰和歡愉的交替中寫文書,若有所失地遞交早申請,然后要么迎接狂喜,要么一蹶不振。但實際上我并沒有夢校,寫的也是平平淡淡的文書。交完ED的第二天,我頭也不回地開始準備RD。在接到defer以后,我既為不能早早下車感到惋惜,也為能夠完整地體驗一次申請季而充滿期待。
不過倒敘好亂,所以我還是從頭開始講起吧。
我的志向有啥呢?我較堅定也較短暫的理想始于小時候的某個陽光燦爛的早晨:我在家里斷定我以后要成為一個prominent的人。當時知道的prominent的女性不多,于是我想到了劉延東——新聞聯播里出境率較高的女性;只是好景不長,上了小學以后我立志發明時空穿梭機回到古代幫助諸葛亮保養身體,與其成為夜觀星象的密友;上了初中以后我想去拜仁慕尼黑當足球記者;看完韋斯安德森的電影以后我想當導演;看完《當呼吸變成空氣》以后我想當神經外科醫生。只有照鏡子時才發現,我還是那個滿眼混沌的學生。
可是想了想,當個學生可能是我較幸福,較有成就感的差事了。我生活在象牙塔的保護之中,享受著相對的公平和相對較高的付出回報率。理想的泡泡還沒被戳破,現實世界陰暗的潛規則也還未被完全揭露。我不用為我的失敗嘗試付出太大的代價,且因為年紀輕,經常能夠得到從頭再來的機會。因此,我覺得如果我能自由選擇自己喜歡的學生生涯,并盡量延長它,慢慢地從理想主義轉向現實,水到渠成,聽上去也不錯。
思想自由和活躍但不死板的學術氛圍讓我選擇入讀中大附中。我喜歡每天早上進入校門時校長、主任和保安叔叔洪亮的“早上好”,喜歡教工排球賽場邊助威的人群,喜歡“東邊”的附小日出,“西邊”的附中下雨的美好景觀。我從初中的剪報欄上了解名人遺言,關注娛樂新聞,認識了不少優秀的作家,也知道了有HFI這么個地方。中考臨近,剪報欄上有一篇關于某中學在校園內貼滿勵志橫幅激勵學生考試的新聞,旁邊是校長用紅筆寫下的評論,問我們能否在脫離形式上的鼓勵以后仍保有上進之心。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下,我睡覺前的腦袋總是被各種各樣的思考和反思所填滿(雖然第二天醒來幾乎都會被忘記)。我發現我之前過于注重課內學業發展,而忽略了自己精神家園的建設;我開始主動給自己設定額外的學術拓展和閱讀目標;同時,我也漸漸堅定了出國讀書的意愿。就這樣,挺順利地,我和一大幫有著相似目標的同學考來了HFI。
高一結束時的我是十分樂觀的。因為入學時基礎不錯,我不用費很多心思保持GPA,所以獲得了很多空閑時間用來看劇,看電影,看書。因為撞大運,我還申請到了挺好的夏校。我發現只要我愿意花時間在一間事情上,會得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因此,當表哥在快放暑假的時候告訴我自己因為工作太累想跳槽回西安的時候,我第一反應就是跟他說:那你可能還不夠努力!這件事聽起來有多勵志,本質上就有多幼稚。
我一直在躲避的事實是,我極其痛恨去認真審視大學申請這件事兒。剛入學沒多久,就開始被逼問兩手空空的我想選擇什么專業。似乎在一夜之間,每個人都擁有清晰的passion,擁有了屬于自己的獨特人設,擁有了為前兩者高調努力,侃侃而談的志氣。我在羨慕的同時感到非常的焦慮,因為我從來沒想到我要這么早就開始思考這些問題。后來,我漸漸發現這些所謂的passion大多是用來制造peer pressure的無稽之談:它們大多只算是好奇心;有時因為假意的故意堅持,passion還讓人忽略了思考方式的多樣性,造就了固定思維。
盡管如此,壓力還是讓我想盡一切辦法否定這個趨勢。我聽到passion這個詞時會捂上耳朵;我對很多事情都裝作不屑一顧的樣子(雖然有時候其實非常在意);我給自己設置了很多條條框框,希望自己不要成為時代洪流的落水狗。我把自己鎖在了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營造出歲月靜好的假象。我走在路上清風拂袖,躺在床上氣定神閑,聊天窗口前妙語連珠,殊不知自己已經錯過了很多良機。
后知后覺的我決定在高二把握住一切機會。
我參加了許多意義重大,但遠在高一時嗤之以鼻的活動。活動日程被安排得滿滿當當,我卻措不及防地被高二滾滾涌來的學業壓力淹沒,失去了睡眠時間和情緒穩定性。同時,因為我選擇了一所ultra-reach的大學作為努力目標,每一次的考試、閱讀、遞交project忽然都與我的未來綁在了一起,使人喘不過氣來。
去年三月,當被躊躇滿志申請的夏校一一拒絕,考試接連翻車,遇到不可描述的不公正對待時,我一整個月都處于極度崩潰和疲勞的狀態。這聽上去有點慘,而我的確也suffer了不少,但是我一直十分珍惜這個挫折。那段很難過的時間,一直有個聲音告訴我這些經歷并不是故意為難我,而只是想幫助我快點成長,在以后能夠更加從容,少走彎路。因此,我可以說是一邊流淚一邊充滿感激地度過了那個月。我除了在宿舍學習到較晚以后怨天尤人,除了走在校園里想不通自己現在的努力到底有什么意義,除了坐在椅子上感覺自己的心跳突然變得震耳欲聾以外,還得到了家長和老師的鼓勵,得到了binge reading的快感,也意外地得到了幾個不錯的消息——當我把這些消息串起來的時候,發現自己似乎擁有了一些亮點和值得努力的方向。一路走來留下的凌亂不堪的軌跡被掃清了不少。我在三月底某個平淡的晚上忽然想通的同時,也愿意相信“船到橋頭自然直”。
高二的我在很多方面沒有收獲到較滿意的結果,而我深知如果我在一開始趨利避害,是可以避免大部分的失望。但如果問我愿不愿意繼續幸運而滿足地度過這一年,我還是會很糾結。有些坑早晚都要踩過去;有些苦澀始終都要去嘗。“經歷”本身大都是中性的,因為它們發生在這個存在即合理的世界。所以就看我自己怎么解讀了。
相比起高二,我的申請季顯得非常云淡風輕。
寫文書的初期我有些煩惱,因為我發現很多在我腦中辛苦醞釀了十幾年的宏大觀點對于別人而言只是信手拈來的common sense。以前總覺得一個人的思想和說理能力是ta存在的較大價值,所以“整體的思想包容性遠大于個體”這個事實讓我瞬間失去了寫作靈感。于是我哭著跟朋友說:完了,我怕是對人類發展做不了啥貢獻了。
后來我的主文書選擇了十分貼近生活的題材。我發現雖然我和很多人在愛好、寫作風格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很多交集,但每個人對于這些特質的不同結合方式還是讓個體獨特性有了發展空間。
過了這個坎兒,后半程的文書寫作成了輕松愉悅的修改和素材的反復利用。因為文書寫作是一個主動探索的過程,讓我感受到自己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命運,所以比起漫長的等待,它是申請季中較為放松踏實的一環。
說到掌控自己的命運,就不得不提選校了。選校的初期我是十分有信心的:即便是reach school,即使看見前人在它面前的慘淡戰績,我也愿意相信我會因為某些優勢沖出重圍。這種感覺就像數學老師發下來一道壓軸題,告訴你還沒有人能夠解出來,然后你就本能地覺得“啊!說不定我就是把這題解出來的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天賦異稟(雖然之前一直成績平平普普通通)的學生啊!”。結果你拿到這道題以后,焦頭爛額,終究是沒做出來,只能像小雞啄米一樣聽老師給你點撥。
申請reach school跟解數學題的幻滅跟有很多相似之處的,但它們還是有些本質區別。解不出數學題可能說明你的功力還沒到,但申請之所以被稱為玄學,不是因為付出得不到回報,成就得不到肯定,而是因為太多人都在付出很多的同時功成名就,因此招生官也很糾結要成全這其中的哪一部分。仔細想想,拋去走后門的走側門的過分genius的體育太好的生活太慘的文化背景太豐富的,仍然有超過學校錄取名額好幾倍的平民申請者擁有著達標的資質、精彩的文書、亮眼的活動和優秀的品格。因此,只要你達到了某個標準以后,你的命運大概更多依賴于那天的天氣、招生官的心情、和你的申請材料一起被審的其他材料,等等微小的因素。
想通這一點以后,不妨把錄取率換算成拒絕率:每一次的拒絕不代表著的否定;相反,每一次難得的錄取都是你和這個學校緣分的見證,值得好好慶祝和感恩。所以,2月16號那天中午,當我沒報太大希望地點開portal,發現學校的吉祥物從電腦屏幕砸到我驚訝的大頭上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是幸運的。
很多學生故事都以自己拿到offer時的欣喜激動而收尾,可是我的這封offer讓我陷入了新一輪的迷茫和焦慮。我發現申請季期間與父母發生的沖突還在繼續,困擾著我的成績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晚自習咸魚的時候反而會加倍地感到頹廢與自責。我保有了將近六年的夢想忽然實現了,但是我似乎并沒有因為這個改變而忽然變得更好。相反,突如其來的不真實感一度讓我懷疑是不是offer發錯了。
以前我滿身疲憊地看著申請季結束的學長學姐,覺得他們身上閃著光;現在我滿身慵懶地看著宿舍走廊讀書學習的學弟學妹,覺得有無數道光正在照亮著他們。夢想的更大意義可能是想讓你記住自己專注、努力、充滿希望的樣子,而它的結果于我而言是狂喜過后的沉思。后來想想,夢想可能只是經歷裹上了糖衣,本質上仍然是中性的。一個個夢想從身邊劃過后,每個人都還在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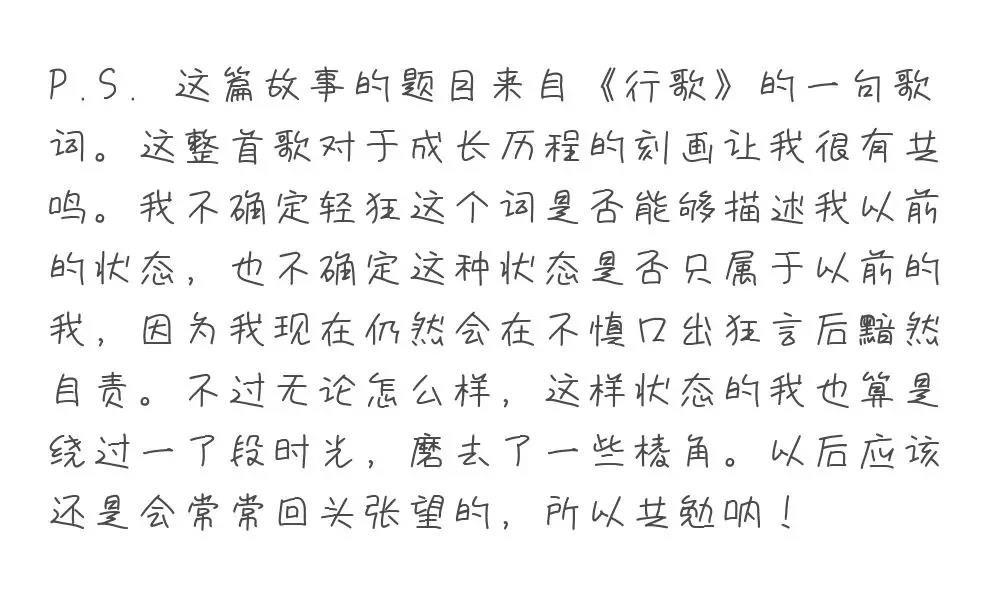
謝謝幫助過我的家人和老師們!謝謝mx,lx,wc,gx,lt,ed,bw,sz!謝謝耐心看到這兒的你!




 公眾號
公眾號






















 服務熱線
服務熱線
